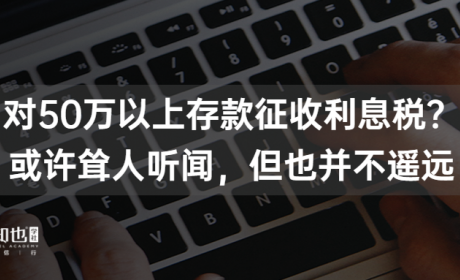究竟需要多少钱,我们才能过好这一生

编辑|彭韧
编者按:人在世上,是否应该永无止境地追求财富?在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看来,随着生产效率的提升,未来的人们可以大量减少自己的工作时间,到时候人们可以把更多时间投入到艺术和创造中,凯恩斯把他的预言写入了他的著名演讲《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之中。
不过,事实证明,凯恩斯的预言失败了,虽然生产效率的确如经济逻辑所推演的那样大幅进步,但是人们的工作时间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是在延长。这让英国经济史学家,也是《凯恩斯传》的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和他的儿子爱德华·斯基德尔斯基决定共同来探索这个问题,并且写下了《多少才足够?金钱与好的生活》。
这本书探讨的是人类生活最核心的问题之一:金钱和财富的意义是什么,个人和社会为何总是需要更多的金钱和财富?通过这本书,斯基德尔斯基父子提醒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经济为什么要增长的问题:我们忙着增长,到底是为了什么?本文选自本书第1章《凯恩斯的预测失败了》。
1928年,凯恩斯面对剑桥大学的一群本科生做了一场演讲,主题为《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凯恩斯知道这些学生对资本主义不抱幻想,他们倾向于把当时的苏联视为指路明灯。凯恩斯早就意识到,进步是一个“被弄脏的信念,被煤灰和火药染成了黑色”,而共产主义的召唤如此诱人,它甚至被视为 “一个伟大信仰的最初萌芽”。
如果凯恩斯要引导他的听众远离这个神明,他就需要说服他们相信资本主义也是一个乌托邦计划,而且会比共产主义更有效率,因为它是实现人类富足的唯一有效的方法。凯恩斯在剑桥大学的这场演讲是他首次袒露自己的乌托邦式理想。
凯恩斯用经济学逻辑进行预测。从历史上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速度来看,凯恩斯指出,如果投入设备的资本持续以每年2%的速度增加,“技术效率”以每年1%的幅度提高,“100年后,进步国家的生活水平将比今天高4~8倍”。这一预测使凯恩斯得出了“惊人的结论”,即“假定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没有大规模的人口增长,那么‘经济问题’将可能在100年内得到解决,或者至少是有望得到解决。”。
凯恩斯的意思是,人类只需要占用眼下工作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的一部分,就能满足全部的物质需求,每天最多工作3个小时即可“满足我们的本性之恶”。由此,剩下的大量时间可能会使人出现那种富裕阶级的家庭妇女因空虚而导致的“精神崩溃”。但是,凯恩斯并不希望如此。相反,他期待这样一个时刻的到来:现在只限于艺术家和自由自在之人的自发、愉快的生活态度,能扩散至整个社会。这篇文章混杂着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以令人赞叹的辞藻将文章推向了高潮。
我认为当达到这一丰裕而多暇的境地之后,我们将重新拾起宗教和传统美德中最为确凿可靠的那些原则,即贪婪是一种恶癖,高利盘剥是一种罪行,爱好金钱是令人憎恶的。而那些真正走上德行美好、心智健全的正道的人,他们对未来的顾虑是最少的。我们将再次重视目的甚于手段,更看重事物的有益性而不是有用性。我们将尊崇这样一些人,他们能够教导我们如何分分秒秒都过得充实而美好,这些心情愉快的人能够从事物中获得直接的乐趣,既不劳碌如牛马,也不虚度岁月,逍遥如神仙中人。凯恩斯的朋友、哲学家弗兰克·拉姆齐,用一个词语“乐土”来形容这种天堂般的状态。
因此,资本主义是一种努力奋斗和赚钱的生活状态,是一个过渡阶段,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这个目的就是美好生活。凯恩斯后来说,这始终是他“内心深处的信仰”。作为一位经济学家和思考者,凯恩斯的大部分人生是在 “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世界里度过的,但他总能腾出时间去追逐艺术、爱和知识。
自凯恩斯写下那篇文章之后,至今90多年过去了。我们是他的“孙子辈”,甚至是他的“重孙辈”。那么,凯恩斯的预言应验了吗?
凯恩斯的预言应验了吗?
凯恩斯的文章提供了两个预测和一种可能性。两个预测关乎“增长”和“工时”,简单来说,凯恩斯认为100年后,西方世界的经济增长将“足够”满足我们所有的需求,所以我们每天的工作时间不超过3个小时。一种可能性指的是,我们将学会如何利用闲暇,过上“睿智、愉快和满意”的生活。那么,这些假设的结果如何呢?
现在,让我们把这两个预测和实际结果加以比较。实际人均收入的增长和凯恩斯的预测很接近,不可否认,这其中有巧合的成分。凯恩斯假设所预测的国家不会发生重大战争,并且人口没有增长。事实上,人类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人口已经增长了大约1/3。凯恩斯也低估了生产率的增长。这两个失误互相抵消,结果就是,1930年以后,人均收入确实增长了4倍,符合凯恩斯预测的下限。
那么,每周工时的下降情况又如何呢?凯恩斯预测,在这样的条件下,每周工时将随着生产率的增长而下降。这似乎是基于常识性的假设:收入存在着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即每一笔额外的收入会产生更少的额外满足,所以,随着社会越发富足,人们越发倾向于拥有更多的闲暇,而非更多的收入。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考虑到每小时的额外产量,他的每周工时将会逐渐减少,直到每小时收入增加的效用等于每小时闲暇增加的效用。
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1870—1930年,每周工时快速下降,凯恩斯假设这种下降的趋势会持续下去。凯恩斯写道:“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也许只需付出过去1/4的努力就能完成在农业、采矿业和制造业上的工作了。”
虽然收入和生产率如他预期上升了很多,但每个人的每周工时自1930年以来远没有达到下降75%的程度。1930年,工业化国家的每个人每周工作大约50个小时;今天,他们每周工作40个小时;而根据凯恩斯的预测,我们现在即使没有达到每周只需要工作15个小时,那也应该很接近这个水平了。如果我们用现在的趋势推算,到2030年,我们也许能达到每周工作35个小时,但绝不可能是每周工作15个小时。问题在于,在“工时的下降大大低于每小时产出的增长”的情况下,凯恩斯为什么会做出那样的预测?
凯恩斯的预测没有考虑地域因素。他可能认为,到2030年,贫穷国家将接近或赶上富裕国家。凯恩斯的预测并非完全错误。东亚个别经济体已经达到西方的经济水平,还有一大批中等收入国家不久也将赶上来。但是,人口的急剧膨胀是他未曾预料到的。1930年,世界人口为27亿;如今,世界人口高达70多亿,是1930年人口数量的2.5倍还多。即使在富裕国家,人口增长也超过了30%。凯恩斯未曾思考的一个棘手问题是:为了帮助穷国,富国需要把抵达“乐土”的时间推迟多久?
凯恩斯的预测为何会失败
平均工时下降并未和收入增长同步,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解释。有人说,人们的工作时间之所以到现在还这么长,是因为他们喜欢工作,或是因为他们被迫如此,又或是因为他们想要得到的更多。
列宁说过:“不劳动者不得食。”凯恩斯遵循他那个时代的经济学,认为工作是为获取必需品所付出的代价。正如亚当·斯密所写的那样:“每件东西的真实价格……取决于为获得它而付出的艰辛。”抑或像杰里米·边沁所说的那样:“如果劳动真正地被人接受,热爱劳动就是自相矛盾的说法。”
这样的看法并无新意,因为《圣经》早已告诉我们,人们受罚做工,乃作为其违抗上帝之意的救赎。但最近,有人指出工作意味着“劳动和辛苦”这个古老的等式并不成立,或者虽然这个等式成立,但其准确程度正在逐渐减弱。
工作不再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劳动”,而是“对劳动的热爱”,是激励、认同、价值和社交的来源。简而言之,工作不只是人们达到目的的手段,它还提供内在的满足感。这就是人们会继续工作,而且工作时间超过了他们的“需要”的原因。
快乐工作的倡导者认为经济学家将工作视为无趣的劳动,它必须以获得的收入作为补偿,这种观点也许适合过去大多数人必须从事的重体力、机械、乏味的工作,但并不适合现在的工作。到了后现代,工作强度不再那么高,工作也变得较为有趣,更富挑战性和创新性。这些特点尤其适用于专业岗位,而且解释了为什么高薪者比低薪者的工作时间更长。我们有一个日益壮大的创意产业,与过去相比,对工作的选择更多是出于必需性。人们不仅从购物中认知自我需求,在工作中也是一样。批评者补充说,凯恩斯对商业有一种布鲁姆斯伯里式的蔑视,这导致他忽视了人内在的满足感,即便在他那个时代,许多人已经在工作中发现了这种内在的满足感。
与“热爱工作”相对的据说是“害怕闲暇”。经常有人问,如果人们不需要工作,那他们会干什么呢?酗酒或吸毒,还是整天看电视?提出这种问题的人认为,人类天性懒惰,所以工作是让他们有价值、走正道、避免堕落的有力选择。他们还认为工作提供了强制的社交机会,而闲暇却迫使人们独处。汤姆·拉赫曼的小说《我们不完美》描绘了一位工作狂记者,他说:“我害怕过周末,我希望没有假期,因为在假期里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好像周围的人都在提醒我:我是一个失败者。”
领取报酬的工作是帮助我们获取内在满足感的因素之一,但大多数人不只是为了面包而工作,否认这一点是不明智的。人们长时间地工作也许是为了友谊,或者是为逃离家庭生活的烦恼和乏味。但是,工作的“愉悦”程度是否与日俱增,这一点并不明确。有些工作变得更有趣,比如互联网使工作更像游戏,也增加了工作中的休闲机会;只需点击一下鼠标就可以浏览脸书网站。工作环境也被设计得越来越“有趣”。
但是,亚当·斯密认为专业化将导致技能与工作分离,也会导致很多工作报酬减少。所谓“技能”,通常是机械化的一种委婉说法,工匠、机修工、建筑工、屠夫、面包师的技能已经退步了,很多工作也沦为例行公事,令人麻木。现代超市和呼叫中心的常规工作被冠以“数字泰勒主义”,这是在向传送带的发明者致敬。大幅削减成本减少了人们“面对面的时间”,但现在这是一个社交新名词。许多工作的“创造性”只是一种品牌推广,比如,一家著名的快餐连锁店打出这样的广告:勤奋而热情的厨师每天都在创新。即使对于高级金融人才来说,工作带来的快乐也远不及工资和奖金带来的满足感。那些高薪人士愿意比过去工作更长的时间,这也许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工作的兴趣增加了,而是因为他们对收入越发缺乏安全感。只有一小部分工作可能变得让人喜欢,但大多数工作仍旧不为人所爱。
尽管人们大多认为工作是快乐的,而且害怕自己无所事事,但是,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多数发达国家,工人更喜欢减少工作量,而不是增加工作量。一项针对未来就业选择的调查表明,人们缩短工时的愿望广泛存在,即使知道这可能意味着工资较低,有51%的被调查对象选择更短的工时,而只有12%的被调查对象选择更长的工时。
相似的调查结果在日本也出现过。在美国,两个数据较为平衡,但被调查对象仍倾向于更短的工时,而不是更长的工时(37%∶21%)。人们的选择是在假设情况下做出的,这并不代表当面临真实情况时他们也会那么做。不过,至少存在着对更短工时的偏好。
工作愉悦感的增加或者闲暇恐惧感的增加,也许可以成为解释工时不再下降的原因之一,但不可能是主要原因。亚当的诅咒也许减弱了,但并未完全消除。对工时未能下降的结构性解释,必须从人类欲望和内在满足感等方面加以补充。
永不知足
凯恩斯假设人对物质的需求总会有满足的一天,但是,倘若人都是贪得无厌的呢?按照字典的定义,贪得无厌是指对自己拥有的东西永不知足。有一条针对“拥有一切的人”的广告说道:“这些‘浪漫的’斋浦尔帐篷(售价3 800英镑)能在花园中挤出来非常棒的娱乐空间。”
问题是,为什么“拥有一切的人”总是想要更多?
有两种方法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第一种是探究个人欲望的本质,第二种是结合其他人的欲望加以考虑。两种方法的对立更多是人为。欲望是个人行为,但它们被表达、被鼓励或被压抑的方式则是社会行为。研究人员选择哪种方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是否对建立个人心理的事实感兴趣,或者假设这些事实是给定的,他能否想到这些事实对社会的影响。
凯恩斯的错误在于,他认为被资本主义释放出来的贪欲可以因充裕而得到满足,人们自此以后便能自由地享受文明的成果。这是因为他认为人的欲望是有限的,但他没想到资本主义会产生一股创造需求的新动力,冲破习俗和良知的束缚。尽管今天的我们更加富裕,但我们实现美好生活的起点相比他那个时代更低。资本主义在创造财富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是我们却无法把这些财富用于文明建设。
人们建立了一种体系,把贪欲从道德的牢笼中释放出来,但却几乎无法把贪欲重新关进道德的牢笼,或控制住它。我们怎么会做这样的事呢?